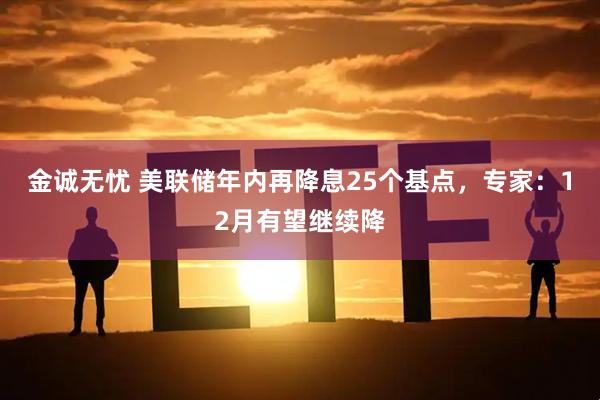嘉善路117弄,新兴顺里,一百多年的老弄堂深处,时间、空间被压缩。
这儿保留着上世纪20年代前后建造时的建筑,没有自行车棚,也开不进汽车。最窄的弄堂仅一米宽,随意一辆自行车斜靠,就能轻易阻断整条通道。但地段优势,让这里的人口密度高,居住面积局促——“60%是租客,剩下的都是老人。”徐汇区天平街道嘉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志阳说。
弄堂里有“龙潭三杰”之一钱壮飞的旧居,又紧挨着永康路,循迹打卡的游客涌来,共享单车也如潮水般涌入,“租客图方便,游客跟着停,老人被绊倒却找不到责任人”。
在上海,老弄堂肌理复杂、密度高,对城市治理提出挑战。

“这儿需要的是‘扎根治理’,根植于在地知识——需要精细感知空间的特质,敏锐体察邻里关系的变化与居民的生活习惯。”天平街道党工委书记曲文倩说,正是基于这种因地制宜,多格合一,依托条块协同、多元参与的民情快办机制,“禁停不禁行”的方案诞生——一旦进入小区范围,共享单车将无法落锁。
如今,这一方案从新兴顺里溢出,惠及街道其他12个同样无门卫管理的开放式里弄、市政道路。
如高安路9弄,这条曾深陷市政与小区管理“夹缝”的150多米必经通道,将被纳入同一套智慧治理网络,“三不管”困局终获破解。

“弄堂议事会”民情快办
年过七旬的社区居民姜仁初,是里弄的夜巡志愿者。隔天就要夜巡摇铃,雷打不动坚持了近20年。“租客游客多了,共享单车、外卖这些新问题就来了。”
弄堂里路灯少,部分支弄没有路灯,时不时有老人被绊倒却投诉无门,“别说骑车人难找,这些车早高峰一过,也常常消失无踪。”
老姜也心疼那些骑单车的小年轻:都是附近上班族,早出晚归,有了“最后一公里”的便捷,却遇上没处停放的“最后一百米”。

居委会不是没想过办法——在弄堂大门口和拐角处设置提醒牌;楼组长和志愿者骨干参与宣传,劝阻单车进小区;安排保安在夜间巡逻时搬走部分单车等,李志阳掰着指头细数。但弄堂四通八达,这边刚搬走,那边又骑进来,效果有限。
老姜的夜间巡逻统计显示:弄堂日均停放单车8-12辆,节假日翻倍;停放高峰集中在晚8点后;80%投诉来自中老年居民。
解决之道需要“治本”的方案。天平街道依托“民情快办”机制——围绕“集、分、办、督、评”5个环节构建闭环,迅速响应并锁定症结。
比如,工作平台接到诉求后,将问题派单至责任部门,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居委会取得联系,实地走访勘察。而后,组织召开“弄堂议事会”,由街道社区管理办牵头,联合区建管委交通中心搭建协商平台,与共享单车三大运营商展开商讨。
方案逐渐清晰:在弄堂口设置GPS电子围栏,精准调整禁停范围,确保一旦进入小区,共享单车即刻触发落锁禁令。
“运营商最初也犹豫。”街道管理办副主任陆鹏飞坦言。这种顾虑源于多重因素:技术调整成本、用户使用习惯改变可能带来的短期流失、以及“谁先做谁吃亏”的观望心态。
对此,街道明确承诺将在后续管理中提供公平的监管环境,通过这种基于数据、诚意与公平的协商,僵局得以打破,三家运营商先后参与进来。
为需求“松绑”
方案上线前夕,美团单车工作人员反复穿行于新兴顺里的窄巷:以用户视角实地取还车,对比坐标数据,精细修正电子围栏边界——直至完全契合弄堂蜿蜒的肌理。
“确保虚拟围栏与物理空间严丝合缝,是治理生效的根基。”美团单车上海市运营经理马起源解释。测绘人员深入巷道,精确丈量每一处转折,密集采集坐标点——“规则区域定四角,复杂地形增标记,务求后台地图与用户所见一致”。规则亦同步硬化:禁停区3次违停扣减信用分,强制锁车后需付费方能解锁。

勒紧秩序的缰绳,也为需求“松绑”。弄堂口外,人行道上框出白线,哪里可以停放单车一目了然。
过去,“跑马圈地”的扩张模式,导致共享单车过量投放与运维不足,将巨大管理成本转嫁至公共空间。非机动车停放问题常被简单归为“秩序管理”或“市容整治”,忽略了其作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关键一环的内核。街道将其有效融入土地利用、交通规划、社区建设等系统设计。
方案实施一段时间以来点金网,违停订单归零,投诉量下降90%。“有成效。”摇铃志愿者们更有干劲了。
大牛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